
今天订购到社区志愿者派送的鱼,有草鱼、鳊鱼、鲫鱼。死鱼腌好,活的养着,鱼儿们一下水便欢腾起来,摇头摆尾。手去触碰,几个脑袋便齐刷刷地挤在一起,争先恐后,一会儿,又裂开圆形小嘴咕噜噜的向我问好。
前天,楼下大姐给我辣子酱,她笑着说:"平时恐怕你们不吃这些,现在给你们,开开味估计正好呢。"
"今天下午我做了几个包子,没有卖相,口感还可以,尝尝。挂你门上了。"这是邻居三秀的微信。"我多买了糍粑、还有面粉,想你也需要一些的。挂你门上了。"这是楼下小啸的语音⋯⋯
望着满桌的菜品,想起了那些看菜、吃饭的陈年往事,恍惚于温暖阳光下,置身氤氲着瓜果蔬香的童年。
在任何情形下,浮现于我记忆中的"老家"一词,要属三排平行排列房子。正屋清一色的白墙布瓦,大多数是"八柱三间",前后整齐、高矮一致,屋后有厢房,屋顶略低于正屋,作厨房用。正屋前面有一平台,我们称之为"活场",用于打场散晒;厨房后面有后院,种菜、种树皆可。家家如此。
在老家,最喜欢的是夏天。好像夏天到了,就有吃不完的瓜果和蔬菜,那些个略带甜味可食的东西,真是取之不尽啊。
后院是不打围子的,也是不准种菜和种树的,说是资本主义。当时人小不懂,只知道爷爷说过:好好的地,荒着真可惜了哩。并万般说服生产队长留下四棵桃树,说儿子媳妇不在身边,四棵桃树留着结桃,也好让四个孙孙有东西吃一吃。记得,桃树上分别刻有我们四姊妹的名字,当树杆粗壮,名字开裂变大,我果真吃上了香脆酸甜的桃子。
后院紧接着是生产队的菜园子。大大的菜园与各家后院之间有篱笆墙,但是,密密匝匝的高枝杆哪里能隔断孩子们香甜的渴望呢?想到圆圆的西瓜、香气扑鼻的香瓜和老鼠瓜,篱笆底部就被扒开好几次。树荫处,清凉脆绿的瓜皮,几掌下去,噗嗤有声,连眼睛都是凉爽的,泛着香气。有时候,扒拉出来略带湿土的红薯,撩起衣角,掐掉两头,呼啦一下,来不及剥了红薯皮,就直接开吃。还有高梁杆、玉米棒等等,边咀嚼着边想,地上是怎么样冒出这么多甜甜味道来的呢?
到了摘瓜果蔬菜的时候,大人们采摘,交给生产队收堆,晚饭时间,通知各家各户到队屋里分菜,一般按每家的劳动力或者人头数分堆。和姐姐提着篮子去分菜,那是我很高兴做的事,虽然有的时候,分到的菜没有别家的多,菜品也不如别家的好看,但我和姐姐总是兴高采烈的,好像家里一下子有菜吃,全是我们的功劳。
最高兴的事情是"挑猪菜"。家里的猪食一般都是米糠煮菜,米糠是有限的,就得增加多的菜叶或者野菜。挑猪菜一般是在堤坡上、河岸边、沟渠旁,这些地方天高地广,透着清香,所以最为开心。记忆中的"挑猪菜"有着蒲公英的色彩,绿的叶、黄的花、白的果,摘下一颗颗绒绒的圆球,小心地捏住茎尾,放在嘴边轻轻一吹,一朵朵白白的小伞似仙子般飘散开来,曼妙迷人。还有"巴根草",它总是那样平静的紧贴地面,力不大难以揪动,只有缝间用手指绕住它的根,不动声色地用力一扯,只听见"嘣、嘣、嘣",根须一处一处断开,我听得到,那声音里透着顽强。看着根部似有若无的水红色,慢慢放入口中,竟然咂出丝丝甜味。当然,"巴根草"不是猪菜,蒲公英、马齿苋、马兰头、薄荷,是猪能吃的。
一般来说,晚饭吃的比较从容。大人们不用上工,小孩也不用上学了,所以桌上的菜也会多上一两个,有了一碗炕茄子、一碗煮冬瓜、一碗咸菜,还可加上炒豆角、焖南瓜。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的晚餐,干净的"活场"上摆放着一张竹床,竹床上是一家人的饭菜,我们几个围坐在一起,一边听爷爷给我们讲"何三麻子的故事",一边抢着往自己碗里、嘴里扒饭菜,奶奶这时候不吃,她总是一边摇着扇子给我们驱赶蚊虫,一边微笑着说:"伢儿们,慢点吃、慢点吃。"有时候,左邻右舍也来听"何三麻子的故事",他们总是带来自家的东西给我们吃,象蒸溜粑、野菜团子。
还记得有一次陪爷爷捉"癞蛤蟆"的情形。傍晚,爷爷一只手拿着长火剪,一支手打着手电筒,我提着口袋紧跟在后面。说实话,癞蛤蟆的样子实在太丑了,灰不溜秋的不说,还背着一身大大小小的疙瘩,看着让人害怕。爷爷不怕,他在池塘边、沟沿、田边和房屋周围仔细搜寻着,感觉有点动静,火剪一扒,手电筒照着,癞蛤蟆就一动不动了,等到爷爷夹住了它,我就赶紧打开口袋装起来,记得当时双手打着颤,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。纵然肉嫩味美,我却临食废箸。
爷爷常说,"饱时不忘饥时寒"、"饱时省一口,饿时得一斗。"所以,当时家里总有咸菜、干菜之类。有一年,爷爷帮别人去湖里打零工,每次总带回一小把菱角藤子,奶奶洗净、晒干、打包后,挂在堂屋与房间的檐椽下,因平常有菜吃,就一直没有吃到干菱角藤。奶奶几次翻晒,总也舍不得扔掉,直到有一天又拿出来晾晒时,发现里面已驻进了四五个肉乎乎的小白鼠,轻柔蜷曲,楚楚可怜。那包干菱角藤也就扔掉了。
后来,我们姊妹几个进城了,爷爷奶奶仍然留在乡下老家。那几年,我们饭量逐日增加,而平时的菜品却少之又少,记忆中就数老家送来的冬瓜、南瓜、红薯印象最深了。炒南瓜片、煮南瓜丁、粉蒸南瓜、南瓜细米糊,炒冬瓜片、炸冬瓜块、冬瓜丁神仙汤,红薯条炒食当菜,蒸煮当饭吃。虽然这三种食材被妈妈发挥得淋漓尽致,不过也总有吃厌的时候。有一次,偶然发现住处的墙脚边有象马齿苋一样的野菜,喜不自禁,就和姐姐在奇角旯旮搜寻起来,准备大快朵颐一番,不料被回家休息的爸爸看到,爸爸黑着脸,生生倒掉了半筲箕的马齿苋。就一直没弄明白,爸爸的生气,是因为那野菜不是马齿苋呢,还是因为我们当时没做作业?扔掉半筲箕野菜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。
随着经济的发展,社会的进步,渐渐地,看菜下饭已成为过去。
又不知从何时起,每天吃些什么?喝些什么?怎么样吃?又怎么样喝?俨然成为重中之重了。每日啖食不重复,餐餐翻花样,反季节瓜果、野生蔬菜,鱼要野生、肉要野味,生猛海鲜,无有不食,直到吃掉了珍稀、吃垮了身体、吃坏了生态。我常以为,吃食要以健康为主,如春天踏青挖野菜,绿色清新,身心一快。可但凡是野菜,多半会带一点苦味,凡菜味苦,却皆可清火。人生,也应该如此吧。
3月2日,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114例,14个市州皆无新增,本市也连续三天新增确诊数为零。疫情消息不断向好,估计过不多久,城市便可解封,我们便可踏青。挖着野菜,品尝岁月,留念温暖,记住味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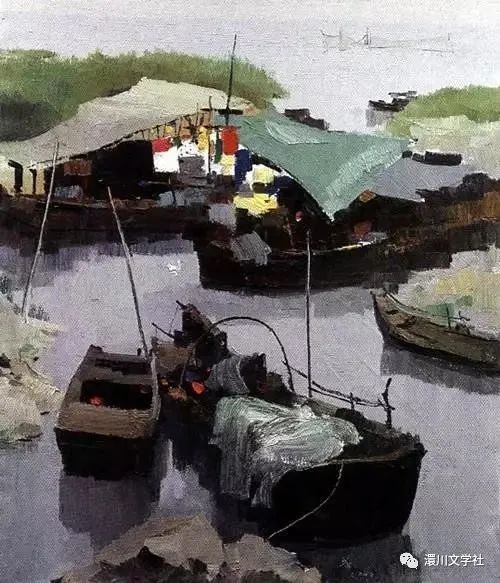

作者简介: 伍红梅 汉川 水利人,昵称捂风挽笑,自小就喜欢《红楼梦》,相信文字能温暖如梦的岁月,相信读书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


